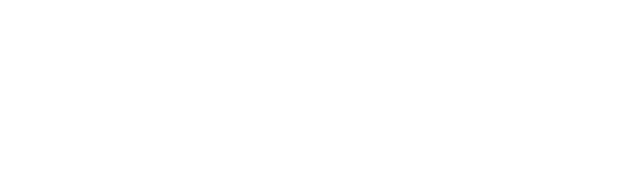太阳底下没有新事,但有新词。
citywalk这词火了。它源自西方,意为城市行走、城市漫步。2023年上半年,国内某社交平台上citywalk相关的搜索量同比增长超30倍。有人说这词的流行就是“年轻人不花钱找乐子”。有人说这是对“附近”“人与人连接”的回归。有人说这只是门流量生意、一种小布尔乔亚的趣味,毕竟,社交媒体上晒出的citywalk帖子,总要加上“很出片”仨字。
关于citywalk,有人花钱请城市导游,带逛大街小巷;有人只是“从熟悉的地方开始,沿着认识的街道走,直到找到不太熟悉的街道”。在社交媒体上,年轻人最流行的玩法是,每来到一个红绿灯,就和朋友猜拳决定,向左还是向右。
无论如何,citywalk暗示的是随意、缓慢、心怀好奇的行走方式。
古今中外,citywalk有很多近义词。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最早提出“闲荡者”(Flaneur)这个概念,用来形容19世纪的巴黎街头上,那些出身世家、教育良好、富有才华妙想,而又喜欢游荡街头、吟诗作画的浪荡子。
词典的简短释义不能完整讲出这词的含义,它隐含浪费时间、懒散之意,但又有“冷眼旁观”“大隐隐于市”的意味。在中国,“轧马路”一词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。“散步”则被认为起源于魏晋南北朝。当时,有种叫“五石散”的药物,药性发作时,人要行走来“散发”。到了北宋,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,苏轼看到“月色入户”,便“欣然起行”,与张怀民月下漫步。他写下“何夜无月?何处无竹柏?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”,成了对散步者心境的经典阐释。
散步是古老的社交方式,是最微小的旅行。
在散步过程中,有人走向的是外部世界。散步让人“了解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空间是怎么来的,经历了什么变化”。纪录片《假装我们在城市》中,作家弗兰·勒伯维茨抱怨,她是纽约唯一会看路的人,也是唯一会低头看到路边镶嵌的铭牌的人。“纽约人忘记了如何走路。”
有人通过散步走向内心。卢梭于晚年写下《一个孤独散步者的遐想》,记录下十次散步中的所思所想。他说:“只有在那时我的头脑才是放空的,我的思维才可以无拘无束地自由驰骋。”
一位上海的资深“城市漫游者”开发出“外滩B面”的漫游路线,给游客看那个屋檐下、缝隙里、弄堂深处的外滩。他会观察上海地面各式各样的花纹、研究上海人从何时起把衣服伸出去晾在外面。有北京的城市漫步爱好者,最爱观察居民用破的自行车、大花盆、甚至装满渣土的油漆桶在胡同路面圈出来的非法停车位。他说:“居民私搭乱建的各种违章建筑——杂货铺、小厨房、鸽子笼,奇形怪状,各式各样,不拘一格,耐人寻味。”
互动出版刊物《北京蘑菇寻找指南》,标记出北京街头存在的大大小小的“蘑菇”形建筑物。很多人在猜这些“蘑菇”究竟作何用,有的说是热力系统散热口,有的则想到“是给地下室透气的吧!”算法在改造着人们的出行习惯,变得越来越高效、功利、点对点,他想反其道,再与朋友约见面的时候,或许可以说“咱俩在西直门东南角的那个绿色大蘑菇那儿见吧!”
人们在与街道的互动中找到“无用”的自由。1972年,几个日本建筑师在东京街头首次发现“纯粹阶梯”,即只能走上去再走下来,而不能通往任何地方的阶梯。后来艺术家赤濑川原平、藤森照信等人发现东京街头许多“无用”的事物,比如无用门(即“用各种方法拒绝人进出的困惑之门”)、无用窗及各类用途不明的道路突起物。
有人评论道,“赤濑川原平的视线里没有任何伤感与怀旧,他冷静平实,心怀批判精神,关注的是物体形状呈现出的怪异可笑感。他不为逐渐消失的老东京流泪,也没有对光怪陆离的新建筑表示愤怒,只是将视线集中到那些在新旧交替的时代里被抛弃到一边、卑微得像个笑话的小东西上,投以会心的幽默感。”
citywalk为什么会火,或许比它是什么更加重要,有人说,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里,唯一能确定的是:今天我们散步吗?